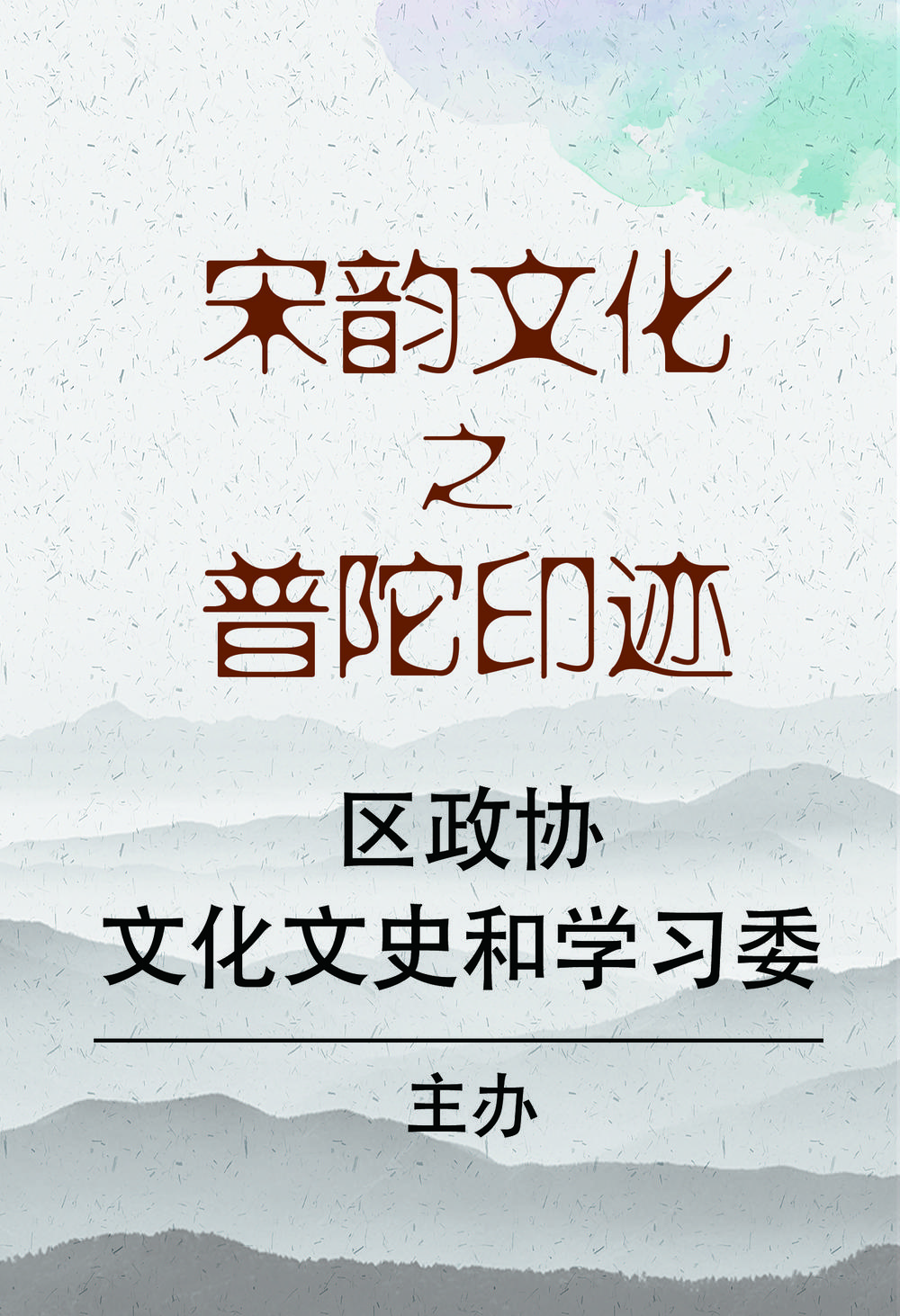□胡瑞琪
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三月,奉命前往高丽国的朝廷使者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奉议郎徐兢等人驾2艘神舟、6艘客舟从宁波出发,踏上了奉使高丽的行程。
根据徐兢后来的记述,从高丽回来时,使团经过黄水洋,第一舟几乎搁浅,第二舟则在午后“三柂并折”,赖宗社威灵,得以生还。当时徐兢就在第二舟上。他说:“同舟之人断发哀恳,祥光示现,然福州演屿神亦前期显异,故是日舟虽危,犹能易他柂,既易,复倾摇如故。”虽然倾摇,终究没有倾覆,还是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一劫。
但这事过了没多少年,画风全变了。南宋莆田人廖鹏飞在《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中说,路允迪使团在路过东海的时候,碰到风浪震荡,舳舻相冲,有7艘船覆溺,独路允迪乘的那一艘船,有“女神登樯竿,为旋舞状”,过了好一会儿,舟船安济。船上有一个保义郎李振,平时是奉圣墩之神的,对路允迪说,站在樯竿上的女神是圣墩之神,是她解救了大家。后来路允迪把事情经过上奏宋徽宗,因此赐圣墩“顺济”庙额。另外一个南宋莆田人李俊甫编《莆阳比事》,也说了差不多的话,就是路允迪也是见女神显灵,在海上救了他们这一艘船。而其它7艘船也是全都覆溺了。
虽然有当事人徐兢的真实叙述,但后世流传的最后还是南宋廖鹏飞、李俊甫等人的版本,完全地以假乱真了。《红楼梦》说,假做真时真亦假,这当然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也包含有更深层次的文化现象。而这个文化现象里面,可能还有两个重要的元素,一个是沈家门的祠沙,一个是普陀山的请祷。
在徐兢的叙述里,使团的船队从招宝山出海,来到沈家门后,曾有过一次祠沙活动。他说,“是夜,就山张幕,扫地而祭。舟人谓之祠沙,实岳渎主治之神,配食之位甚多。”具体的做法是:“每舟各刻木为小舟,载佛经粮糗,书所载人名氏,纳于其中,而投诸海。盖禳厌之术一端耳。”后来他们在行经黄水洋前,还有一次祀沙活动。“则以鸡黍祀沙,盖前后行舟过沙,多有被害者,故祭其溺死之魂云。”这“祠沙”“祀沙”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同,“祠”的是岳渎之神,“祀”的是溺死之魂。因此祭品也各不同,一个送的是“佛经粮糗”并“人名氏”,一个送的是“鸡黍”。前者是要告诉岳渎之神,如今我们这些人要出海,麻烦您来一一照顾,保佑我们平安。后者只是安慰溺死之魂,给你们送吃的,请你们不要来纠缠我们。那么,使团“祠”的岳渎之神是谁呢?徐竞没说,因为是出海,这岳渎之神肯定是海神无疑,问题是哪位海神?在徐兢看来,那位海神或许应该是“福州演屿神”,毕竟在黄水洋遭难时徐兢看到的就是他,但后世的说法,则这位海神肯定是妈祖,也只能是妈祖。
徐兢看到的福州演屿神是哪位神仙呢?他的名字叫陈延晦,是唐朝末年福建观察使陈岩的长子。据《淳熙三山志》所说,黄巢起义后攻陷福建,陈延晦看唐朝已经衰落,心里非常难过,又恨自己手无缚鸡之力,所以对人说:“吾生不鼎食以济朝廷之急,死当庙食以慰生人之望。”他这是说生的时候无力帮助朝廷,死了之后要救护百姓。于是他死后,就成了连江演屿神。福建连江一带的渔民更把他当海神供奉。徐兢遇难时看到他,自然是因为同船上的舟子中有连江的渔人在。但是在沈家门祠沙时祠的岳渎之神肯定不会是这位男海神啊,因为演屿神只是一个地域性海神,不是福建连江一带的人,肯定不会想到他的。
实际上那个时候官方相对认同的还是普陀山的观音菩萨。
徐兢在普陀山时有说:“旧制,使者于此请祷。”就是说在普陀山向观音菩萨祷告,早已经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必须要做的。因此他们在普陀山上请僧人做祷告,官吏兵卒皆虔恪作礼。“至中宵,星斗焕然,风幡摇动,人皆欢跃云:风已回正南矣。”但观音菩萨虽然救苦救难,普渡众生,毕竟不能算是海神,所以他们的请祷,也就只是让大家出海能顺风顺水。这一点,观音菩萨是做到了的。第二天,即将离开普陀山时,朝廷官员再一次做祈祷,“投御前所降神霄玉清九阳总真符箓并风师龙王牒、天曹直符引五岳真形与止风雨等十三符。”这个祈祷,则是祭拜道教的神祗。也就是在普陀山上,使团做了两次祷告,一个佛,一个道,佛道并存,这也是当时普陀山地位的真实写照。普陀山,历史上又叫做梅岑山,它的最早主人,是道教的梅福。观音菩萨落住普陀山之后,还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将其作为自己的道场。
这一次又一次的祭祀,看上去也是比较繁琐的,做起来当然更是麻烦。而最后到底谁能保护使团的人安全出使高丽,恐怕使团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这就像军人打仗一样,令出多家,谁也不知该听谁的,那一旦仗打起来,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的,肯定是一团糟。所以要把指挥权统一起来,归于一家。同样道理,这海神太多,既不利于大家的信仰,也不利于海上救难嘛,所以也要有一个统一,要把多个海神变成唯一的一个。这个唯一的海神,官方最后选定的就是妈祖。
妈祖在历史上是有真人存在的,她的名字叫林默,是福建莆田贤良港人。她的父亲叫林惟悫(一作林愿),官都巡检,母亲王氏。据说林惟悫平时行善乐施,有一次礼大士求子,然后王氏梦大士给她一个药丸让她吞下,吞下药丸之后王氏就怀孕了,生下来的孩子就是林默。据说她出生那年是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出生时“霞光射室,异香氤氲。”古人常把这种天降异象而出生的孩子看作是非凡人,林默当然也是这种非凡人,因为她出生时不哭不闹,所以被取名为林默。林默10岁时就能够背诵佛经了,12岁时有老道士来授她玄微秘法,15岁开始为人治病,常渡海到湄洲救助海上遇险船舶。那年秋天,林默的父亲同兄长出海北上,时西风正急,狂涛震荡,林默本来在织布,忽然就闭上了眼睛,但仍是一手持梭,一脚踏机轴的样子。林默的母亲不知原因,以为她偷懒睡着了,就去拍她的肩膀。这一拍,人是拍醒了,林默手上的梭子也掉地上了。林默对母亲说:“阿父无恙,兄殁矣!”不久林惟悫归来,说在海上遇上狂涛,几次差点溺舟,但冥冥中似乎有人在主导他们的船舵,使他们得以脱险。但儿子所在的那条船没那么好运,舵折而亡。王氏这才知道女儿当初突然闭眼是怎么回事,但后悔已经无济于事。第二天,他们在海上找到了林默兄长的尸体。此后大家都知道林默的事情了,把她认作了海神。28岁时,林默在湄洲峰最高处,升仙而去。
在这样的民间传说中,林默的身份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她既有观音的助力,又有道士的授法,是佛道两家共同打造的形象。而这,恰恰符合中国传统中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想。因此在释道打造的过程中,儒家又参与进来,共同推波助澜。因为民间的信仰最终需要官方的认同,才可能上升为全民的信仰,所以儒士们的参与,最终的目的,就是得到官方的认同,林默的海神形象其实是这么促成的。
路允迪出使高丽途中在海上逢凶化吉这件事就成了妈祖海神获得官方认同最好的契机。在这件事上,放弃演屿神而选择妈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代士人信仰中的女性化理想。像观音菩萨是外来的菩萨,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观音也是由伟丈夫的形象逐渐转化成了女性,最后也是在宋代定形。而海神的形象,也是如此,陈延晦的演屿神形象并不符合中国士人及其民间信众内心的理想,所以他虽然早于妈祖而存在,最终却还是要被妈祖所取代。表面上看是由路允迪出使高丽这件事引发的,实际上这里面是有一个过程的,只不过这个过程比较短,到南宋时已经定形。而借着官方的认同,在妈祖成为唯一海神的同时,路允迪使团在沈家门的祠沙、在普陀山上的请祷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妈祖信仰的发源,是要与这两个元素相融的。
路允迪回到朝廷之后不久,宋徽宗诏令给妈祖以“顺济”庙额,但同时也给了演屿神以“昭利”庙额,但不久之后的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宋高宗赐妈祖“崇福”,次年又赐“灵惠”,又过一年,第三次给赐“灵惠昭应”。这一次又一次几乎紧锣密鼓的颁赐,使得演屿神最终黯然退场,妈祖的海神形象彻底地成为独一无二的了。后来清初有一个叫毛奇龄的萧山人,在其《重修得胜壩天妃宫碑记》一文中说:“若夫神名天妃,旧传秦时李丞相斯于登封之,顷出玉女于岱山之巅,至今祀之,所称神州老姆是也。特以地祗主阴,故妃之。而以所司河海为职土之雄。逮宋元祐中俗称莆田女子契玄典而为水神,此则后人所附会者。”毛奇龄认为妈祖最早的形象并非出于宋代,而是出自秦朝时的神州老姆,莆田女子林默是后人附会的。但他的这个观点却无人理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经过历代文人助推、官方认同,林默的妈祖形象已深入人心。毛奇龄无论如何别出心裁地考证说明,别人也都是一笑而过,不当回事了。